深夜里的百公里
写作是一件会把人吞噬的事情。要投入、要热情、要心无旁骛。年岁渐长,才慢慢想通——所有事情的原本,其实都是生命的一种消费方式。就如同我坐在这里打着字,时间如斯分秒流过,现下我生命长度的这一部分,就全都倾倒在了伴随着窸窣敲打声的思绪里,无可回头。
但我并不想草草了事,即使随心所至,也想尽可能有始有终。
壹·零
有一部电影,名字叫做《深夜前的五分钟》。讲的是一对双胞胎姐妹如玫与若蓝,拥有着完全相同的外表和截然不同的性格。一场海难过后,双胞胎姐妹只回来了一人,另一人永远葬身大海,却没有人知道,回来的这一个,究竟是如玫还是若蓝。
生活就像这一场海难。
我不知道活下来的究竟是哪个自己。
贰·零
高校百英里接力加上武汉马拉松的两次活动后,在这样青春与热血的年纪里,年轻人们总是更容易熟络起来。
左使真名叫杨骁,他说左使二字是取自金庸小说里“左使杨逍”的名号。
也许年岁比我们略长些,左使总是更沉默和内敛。不论打趣还是调侃,他总要比别人多收着一分;幽默起来也毫不张扬,想法常常体贴又细微。
但我知道,无论如何地温柔,会去跑超级马拉松的人,性格里总存在着旁人所不能理解的不妥协;哪怕是偶尔折衷,举手投足间的倔强也无法隐藏。
他说,不是“喜欢”超马,也不是到终点的那一刻才叫做超越;是喜欢准备超马那段时间里的自己——为了一个目标且不计较其中种种,享受身体如此这般点滴的变化。
是他让我想起了《<跑步日记>导演手记》里,梁欢形容蔡宇的一段文字:
然后我见到了蔡宇,这是一个极端内敛的家伙。素人难拍,内向的素人就更难拍了。……后来我们一起吃了两顿饭,聊了很多。这是一个极端偏执的家伙,只有讲自己跑步经历时两眼才会放光,极度亢奋,嘴里会不停说话并且留给你做惊叹反应的时间,其他任何话题他都埋头吃饭。我喜欢这个家伙,我决定要拍他。
也忘记了起因究竟是什么。大概是闲时聊起来,左使说,因为报了佛山超马,想毕业前,在东湖绿道跑一次12h的超长距离,而且得超过自己的PR,跑到100km。——此时的嘴边的100km,也许仅是他日常读书受启发的一个念头,如同在一把不知名的种子里单挑了一颗握在手里,盆与土尚未备好,这种子也不曾种下。
整个5月,队友天水都在准备武汉7月份横渡长江节的游泳比赛。观摩“横渡长江选手”的泳姿只是借口,实际上是为在几个毕业生离校前小聚——队友们一起约着游完泳,吃着烤肉,酒过三巡都已微醺。提起左使的100km计划,向来不喜欢跑田径场的天水,借着酒劲怂恿他:“别跑操场了,多没劲,也难跑下来。你刷绿道,老铁陪你。”
于是,边吹着牛边拍桌子,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——“你来跑你的100km,你跑,我们陪”。也许因为性格里随性的成分作祟,我们都抱着世界末日将至般“择日不如撞日”的心情。
做不到的才叫吹牛呢。
做到了,就得把“吹”字去掉,单剩一个“牛”字。
你就做好你的种子,我们来当盆和土;当然,仅仅有盆有土还不够,浇水、施肥、按时日晒遮荫的事情,也请交给我们来做吧。
叁·零
东湖绿道,不管是跑步还是骑行,山山水水早就烂熟于心。跑前的一天,我和左使确认了路线;考虑到补给和陪跑小分队的方便,标定的露营地点在楚城门外的服务站。细心的他,还专门列了清单出来,不仅写清了他的计划,连陪跑小分队的饮水食物之类都详细周到。原本计划是带足补给,18点抵达露营地点,搭帐篷建立补给大本营。天水、官官、木木和我一共4个人,以轮流接力的方式,每人1-2圈陪左使跑完100km的连续环线;每圈距离约14.75km,每圈爬升164米,累计爬升约1500m。
-14dc865debe860fe0efe16865f692fed.jpg)
而我,却没能按原计划及时抵达大本营。忙完一天,等回到宿舍,已经是21点;他们起跑第一圈下大雨时如何手忙脚乱,我也全然不知。匆匆洗了澡,收好了东西,给木木打了电话,启程出发。木木说,方老师也来了,正在陪跑第二圈。
“其实你不来我们也能理解,毕竟…”
“你们当然会理解。”我说,“不过,我还是来了。”
途中碰上了方老师,刚跑完两圈、累计跑了将近30km的他,看起来仿佛像郊游过后那样轻松愉快。对于武汉理工大学马拉松俱乐部里的我们几个学生来说,方老师永远是“定军山”一样的存在;雷打不动每周一次半马,配速总是很稳,他是凝聚着整个队伍的精神领袖。方老师喜欢把我们叫做“小伙伴”,而他自己,性格也是纯粹热烈、温暖和煦。
肆·零
等我抵达大本营,已经将近23点。此时,天水一圈、方老师两圈,左使总计已经完成了一个全马的距离;第四圈,木木刚陪左使出发,就被我碰上了。看样子还好,左使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疲劳感;木木则是一直以来的小可爱状,欢乐得不行。
以左使日常跑走结合、日跑量50km的水平,恐怕全马还没有到达他的耐力线;真正的体能极限所带来的考验,我并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刻抵达。
我能做到的,只有等待与陪伴。我能选择的,只有无条件相信他。
到达露营点,天水正拿着便携灯,躺在帐篷里打蚊子。
听见声音,他抬起眼一瞟:“你还是来了啊。”
“嗯。不来,我怕我后悔。”
知道我忙了一天有些累,天水让出了帐篷给我,裹着防晒衣躺在了旁边休息站的长凳上。过了一会儿,大楚跑团的呆呆赶了来;这样一来,加上方老师和因大雨没能成行的非也,我们的100km陪跑计划就又多了一个人分享。
简单几句交谈过后,呆呆便顺着出发的方向追了上去。
没吃晚饭的我,就着水,狼吞虎咽地吃了半盒方老师带来的寿司。想了想自己稍有不慎就罢工的胃,我蜷在帐篷里,跟官官说:“你接第五棒,让我消化会儿…”
官官这时还在神游,穿着工装长裤,跑鞋也还没换。
他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,一脸的轻松坦然:“还早着呢。我都可以啊,随你。”
过了一会儿,官官惨叫了一声:“握草,忘带短裤了!”
想起上次合肥半程,我忘记带运动Bra而只好穿着钢圈内衣去跑完半马的囧况,我默默地没作声。
天水揉着眼睛说:“不然我的短裤借你?”
官官语气里满是懊恼,有种自我惩罚的意味:“算了算了,就穿长裤跑。大不了,汗湿透了贴着穿。”
已经是午夜时分,夜跑的人们早就不见了踪影。只剩巡逻车穿梭在绿道,偶尔也路过几队进落雁岛垂钓的发烧友。天空蒙蒙地笼下来,雨后的空气黏腻潮湿,蒸腾起来的雾滴紧紧贴在皮肤表面。不远处是湖水擦过岸边的碎响,夹杂了几声蛙鸣;几只蚊子飞飞扰扰,不算嘈杂却也不寂静。
我躲在帐篷里,听天水和官官有一搭没一搭带着倦意的闲聊,心里想的,是木木、呆呆和左使三人在几公里外的脚步。
一阵窸窣的声音,一大一小两只橘猫晃晃悠悠地巡逻过来,嗅嗅望望。
“咪咪咪……”天水一副想逗猫的样子。
“啾啾啾……”我对自己猫磁铁的体质很自信。
“……你这是逗狗子的声音吧……”
橘猫警惕地看了一眼帐篷,扒拉了两下便跑走了。

伍·零
三个人跑完第四圈时,接近1点钟。左使看起来疲意微然,在休息站的凳子上坐下,和木木、呆呆断断续续聊着,天水和官官忙着倒水拿补给,给左使松懈紧绷着的肌肉。60km不到,还剩将近一个全马的距离。休息片刻,第五圈就又出发了——倔强的穿着工装裤的官官,显然刚热身的呆呆,和若有所思的左使。
忙了好半天,木木喊着热,瘫进了帐篷,没过一会儿就歪着要睡着的样子。天水也钻了进来,继续裹着防晒衣蒙头大睡。橘猫舔着爪子,又两步一停地凑到我跟前。我两手一摊,橘猫闻了闻,左翻右翻,还是半蹲在了离我不远的地方。
剩下沉默的我,在凌晨两点的夜空里,有些不知所措。
我偶尔会失眠。和失眠一起袭来的,常常是直截了当的痛苦,难以名状。
如果我没有来,我只是深夜缩在床里的无数个没有入睡的人们之中,普通的一个。
可是,我来了。此刻的我,就有些许的不同——既不渺小、也不伟大,却再没有了直白的痛苦。
陆·零
帐篷动了动,是半睡半醒的木木在打蚊子。
看了下手表,已经过去80分钟。
“他们怎么还不回来?” 我拖出水瓶,咽了几口水,有些焦虑地望向没有路灯打亮的楚城门。
天水被防晒服闷了一额头的汗,托着下巴说:“这一圈应该是老铁的撞墙期。下一圈我也陪着跑,我说过的,后半夜老铁最痛苦的时刻,我得陪着。”
过了十几分钟,头灯晃动的影子,伴着两个有节奏的声音远远地来了。回到休息站,左使一屁股坐在凳子上,身上的汗直滴下来;官官则是从头汗湿到了脚踝。饮水、补给,这一站休息的时间好像格外长一些,这一圈下来,左使的疲惫感再也藏不住,彻头彻脚地透出来,话都不愿再多说。
我一直觉得,人的身体是有抗性的。所谓训练,不过反复强迫身体克服本能,把自己逼近极限。但更神奇的地方反而在于,人的身体是有记忆功能的。在每次抵达体能极限之后,经过恢复期,身体就会储存这种状态,准备好接受更长久的刺激。
耐力训练,正是这样不断去抵达和超越。
我们四个人当然知道,现下他已经到了耐力耗竭的状态。却没有一个人,此时想跟他说“太累的话不然就此打住”——一丝可能也没有。如果累,可以慢慢跑,可以多休息一会儿,却万万不能喊停。此刻的停,便意味着丧失了这之前7小时里所做努力全部意义。
而我们所应当做的,是假装他并没有跑过在此之前的75km,是从零开跑,是轻松上阵。
柒·零
2017年6月2日,2:57,第六圈,我、天水、左使出发了。
出发节奏尚且保持得不错,过了半程还保持在545左右的配速。三个人不近不远地跑着,两个男孩子话多些,偶尔我插得上一两句。
“一起失眠的感觉,真好。”
郊野道疏影斑驳,风吹过耳边,有躁动的声音。凌晨四点,是鸟儿最是清醒,却是队友疲惫到极点的时候。每一秒的沉默,都是他力竭的痛苦;这痛苦并没有任何能即刻排遣的办法,只能硬生生地扛在肩上、流在血液里、甩在脚跟后。普通人跑半马、全马时经历过生不如死的撞墙期,在队友这里硬是压到了60公里后;而剩下的40公里,明知其中没有任何欢愉,却还是全盘照收。
我不知左使这是哪里来的勇气,却又清楚地知道这是他哪里来的勇气。
“别怕,我们陪着你呢。”
左使看看手表,嘴角藏不住笑:“超过个人记录了。”
我和天水傻兮兮地欢呼了一下,左使撇了撇嘴,表示再没多余的力气雀跃了。
从此刻开始的每一步,都是前所未有的一步。
道旁的小狗早已经打架打累了,见我们路过,佯装气势汹汹,吠了几声。接近郊天台,四下本就无人,此刻一丝光亮也不见,磨山道麻麻的黑了一片;七八米外堤下明晃晃的湖水,这时也被雾气蒙得静谧不少。也许因为两宿没睡,我不争气的腹肌还是抽筋了。大概担心我怕黑,左使跟我并排跑着,间或聊几句,也是他一如既往地提醒我们注意路况。关掉头灯、三个人夜里在磨山深处听虫鸣鸟吟,尘世喧嚣一概不提,现下只剩奔跑与狂欢,以及队友体能耗尽时真切的痛苦;所谓感受生命,大抵如此——它既不在小说中,也不在电影里;它不在别处,就在此时的气息中和唇齿间。
楚城门这就到了,节奏也不觉提了起来。配速员的任务,我这次又没有当好。自始至终我所做的,是尽可能去理解和感受左使以及陪跑小分队中每一个人。
是热烈得没有藏身之处的青春呐。
-9074443b6d93a7935bfff3eda18a3026.jpg)
捌·零
回到露营点,官官已经在等我们,工装裤干了四分之一的样子;经过一夜的劳顿,木木原本还在闷头大睡,听见声响也揉着眼睛醒来了。左使表示肚子麻木到再吃不下东西了,而我身上的衣服也早就都湿透了。服务站里换好干燥的衣裤,和其他人各自收拾好东西拔营,带着行李一起骑车陪他跑完最后几公里。
夏日时分,刚刚5点,天就喏喏地要亮了。我们三个前前后后地跟着,木木则自告奋勇地要跑完她承诺过的最后几公里。再次路过道旁的小狗,狗困得只是抬起眼睛假装要吠起来,就又趴下睡着了。
渐渐明起来,清早赶着上班的清洁工们、欢乐的清晨骑行的大爷们、陆陆续续来晨练的跑者们,一个个和我们擦肩而过。
东湖从天亮到天黑再到天亮的样子,我们见过了。
到湖中道的尽头又折返了一段,左使按了手表。
100km!
然而狂欢的时刻,其实早就过了;这一刻,恐怕大家都累得无暇回想过去的这12小时吧。骑行回学校,匆匆在食堂吃了早餐,五人组个个已经累得七歪八斜,各自回去洗漱整理。
-af6a2aacb8dea4c2395a62de5ad5e20b.jpg!w660)
玖·零
晚上聚餐,除了五人组,
席间,全马破3的呆呆说,不要叫我大神。
呆呆的话,让我想起了这首歌。
So let me go
I don’t wanna be your hero
I don’t wanna be a big man
I just wanna fight with anyone else
Your mascarade
I don’t wanna be your part of parade
Everyone deserves a chance to
Walk with everyone else
——《Hero》,by Family of the year
很多事情其实都像谈恋爱。
在一些时候,事情的“本”与“原”会被淡忘,你我慢慢被“形式主义”绑架。
但在另一些时候,原与本长久地留存在心里,不管过了多少个年月,心境虽然有所改变,初衷却始终不曾变过。
拾·佰
木木说,喜欢这张照片,理由是:“照片中左使在最前面,我跑步跟着,官官和天水骑着车背着帐篷背着物品,小姐姐在最后面给我们照着照片。很和谐很暖心的一幕。”
至此告一段落。
但你我都知道,这并不是全剧终。
以上内容已推送至个人微信公众号 ShevvyOnTheWay 中 深夜里的百公里 。
本文著作权归作者本人所有,未经许可不得转载。文章仅代表作者看法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如有不同见解,原创频道欢迎您来分享。来源:爱燃烧 — http://api.iranshao.com/diaries/197072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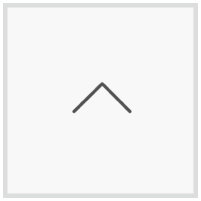

回应
回应
回应
回应
回应
回应
回应